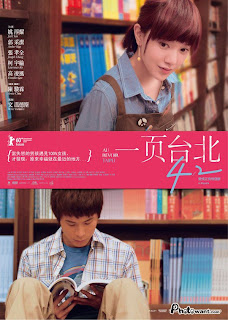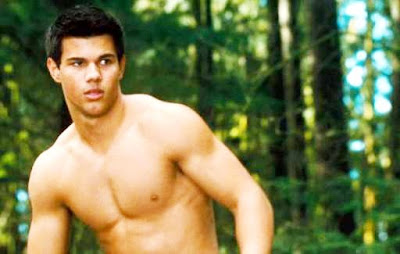《珍愛人生》(Precious)談的是一個貧窮非裔女性如何反抗命運的故事,「貧窮」、「有色人種」、「女性」三者身份相對於資本主義的、白人的、男性沙文的傳統美國社會來說,都是處於弱勢族群的角色,鮮明的弱勢者符號,也幾乎註定了觀眾必須施予同情的角度。幸而導演李‧丹尼爾斯 (Lee Daniels)用割裂的剪接以及仿紀錄片式的鏡頭晃動或拉近/拉遠,稍稍冷卻了濫情的可能。不過,我並不僅僅因其較為收斂的氣氛營造而感到滿足,而是試著想要在這個人奮鬥史之中,看見更多的意義。值得慶幸的是,這個貪婪的要求,在電影對於旁支人物優秀的形象塑造下,竟也順利的獲得滿足。
《珍愛人生》(Precious)談的是一個貧窮非裔女性如何反抗命運的故事,「貧窮」、「有色人種」、「女性」三者身份相對於資本主義的、白人的、男性沙文的傳統美國社會來說,都是處於弱勢族群的角色,鮮明的弱勢者符號,也幾乎註定了觀眾必須施予同情的角度。幸而導演李‧丹尼爾斯 (Lee Daniels)用割裂的剪接以及仿紀錄片式的鏡頭晃動或拉近/拉遠,稍稍冷卻了濫情的可能。不過,我並不僅僅因其較為收斂的氣氛營造而感到滿足,而是試著想要在這個人奮鬥史之中,看見更多的意義。值得慶幸的是,這個貪婪的要求,在電影對於旁支人物優秀的形象塑造下,竟也順利的獲得滿足。在《珍愛人生》中出較有戲份的角色幾乎都是女性,尤其圍繞在主角身邊最重要的幾個人物:由莫妮卡(Mo'Nique)飾演的母親、由寶拉巴頓(Paula Patton)飾演的語文教師,更是各自代表了一方的勢力,在女主角珍愛(Precious,嘉柏莉西迪貝 Gabourey Sidibe飾)的身上,展開一場權力的拉鋸。這幾個角色的演出,交織出更精彩的圖像。
父權社會中賦予男性征服、佔有女性(以提供「愛」與「照顧」做為包裝)的權力,使得珍愛的母親失去保護女兒的勇氣;而顢頇的社福體系對於個案訪查的工作,既無能為力又虛應故事,更造成珍愛悲慘人生的延續。由此可見,珍愛面臨的境遇,是整個結構的壓迫,而不是個人運氣的不佳。既然是結構的問題,勢必不只有一個人會面臨相同的處境。珍愛在文學課堂上的同學們固然同樣是體制中的受害者,其母親以及語文教師──這兩個牽動她生命的長輩──其實也都碰到「如何去面對體制壓力」的難題。她們對於生存之道選擇的差異,也造成了後來截然不同的境遇,而以她們為首的兩個場域:家與寫作班,也呈現了極為相異的氣氛。

毫無疑問地,直到最後一場大告白之前,珍愛的母親在電影中並不是個討觀眾喜的角色。單單見她好吃懶做、指使女兒,甚至是連珠砲般還帶有節奏感的長串俗話狂飆,都在電影敘事偏向主角立場的情況下,通通被歸入反派的形象中。然而,在最後她對著社工與女兒一場憤怒揉和著悔恨的宣洩,卻幾乎又激起了觀眾的同情。導演在這場戲的鏡頭處理上,幾乎與珍愛向社工吐露家庭實情的戲差不多,也就是說,雖然珍愛的境遇極大部分可以歸咎於母親的責任,但是電影並未對兩人進行道德上的揚抑褒貶。這種冷漠的觀察角度除了避免過於濫情的目的外,其實也可以解讀為對珍愛母親境遇與行為動機上的同情,沖淡掉了對其行為後果的譴責。
珍愛的母親在面對體制壓迫並非沒有憤怒,但是在行動的策略上,她卻試圖由體制內的方式爭取自己的空間。當她面對丈夫行逕的忍氣吞聲時,代表的不是默許,而是為了確保得到男性照護的羽翼而做出的交換。而悲劇的是,這樣的策略非但無法奏效,同時還使得她自己也成為壓迫體制的一部分。所以,儘管珍愛的父親在鏡頭中出現的極少,但是他的存在仍然嚴重地干擾著這對母女相互理解的可能。珍愛的母親不斷地動用她的權威身分來規訓女兒,宣洩的是她對女兒性吸引力的憎恨;而珍愛也因著父親帶給她的身心創傷,永遠失去了與母親和解的可能。

面對母親的規訓,珍愛的反抗之路是由寫作的學習開始的,而給她這份武器的語文教師蕾恩小姐(Ms. Rain),自然是與她母親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膚色上蕾恩小姐與珍愛的母親同樣是有色人種,但是在性傾向上,她卻是個女同志──一種可以完全與「渴求男性」劃清界線的身分。我無意聲稱對父權的反抗必須如此絕對,而是將它讀成一種象徵。這種激進的絕裂使她一切行事都剛強而自主,反而能為自己掙得應有的尊嚴與生活空間。
在蕾恩小姐的帶領之下,一對一教學(Each One Teach One)寫作班儼然是個小小的反抗軍。這個班級的成員幾乎都是女性,只有一個鏡頭偶然出現男性學員的影子,而且他還沒有其他的戲份。這些學員們將照顧珍愛的男護士「虧」到羞赧無言,展現了與現實世界倒置的性別權力位階,由此看出這些「惡女」如何跳出了父權的規訓;而她們之間由對立走向親密的關係,和珍愛與母親之間日益嚴重的對立相比,又彷彿是女人應該如何對待女人的深刻寓言。
從珍愛家與寫作班的對比中,顯示出珍愛的人生不僅只是一個力爭上游勵志故事,也可以看成一卷女性運動的面面觀。而從這個角度切入,來看嘉柏莉西迪貝、莫妮克不符時下對女性外表審美觀感的造型時,似乎又有了另一種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