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一般台灣電影,即使票房不佳也還能獲得國際影展認可的優異表現,台灣的動畫電影受限於所需的資金門檻比一般的電影更高,迄今能夠令人激賞的作品仍然是屈指可數。身為動畫製作產業的一份子,其實是非常期待在金穗獎的動畫入圍片中,看到動畫電影未來在台灣發展的契機。
本次入圍最佳動畫獎項的五部片子,片長都是短小精幹,時間與出場人物只足夠般演一個短小而簡單的故事。同時,除了《幸運兒》一片有導演本人配上旁白與音效外,都沒有任何的對白,當然也無法聽到配音員的演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導演以影像說故事的功力自然是被突顯的;但是換個角度來說,這樣的製作方式不僅距離業界的運作模式遙遠,恐怕跟一般觀眾願意觀看的作品也有不小的距離。
當然,受限於資源的不足,用這樣的理由去看這幾部入品其實是不太公平的。所以,在針對動畫入圍片的觀察上,我還是傾向從說故事的功力來看這些作品。
我比較失望的是,兩部在動畫執行的技術比較成熟的作品《紅色月亮》以及《根》,在故事的敘述上都不甚令人滿意。
《紅色月亮》以驚悚片做為嘗試,在一片歡樂可愛的動畫世界裡果然新人耳目。然而電影內容除了看到男性上班族心裡的不安與忿恨外,似乎看不到更值得深入挖掘的主題。先天不良的情況下,讓片中一切反常的、激烈的影像看起來徒然令人錯愕。
《根》有不少大場面和激烈的動作,初看時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可惜後繼過多的時間被花費在動作大秀裡,使得故事沒有經過足夠的開展就畫上了句點,枉費了那充滿濃濃奇幻風格的影像。
相較之下,另外三部片子在故事的敘述上較為引人入勝,但是場景、畫面帶來的視覺震撼力就沒有前二片來得高。
《歐椰!!》就是用最簡單的角色與場景,明確地說出一個合作的故事。故事的內容稍嫌老掉牙,不過節奏的掌控是適當的。比較可惜的地方是,既然兩個角色明確地在暗喻當今台灣社會藍綠兩大政治傾向,在情節的設計上如果能夠兩貼切地比擬雙方爭鬥時當見的戲碼,會使得這部作品更加完善。
《幸運兒》的童音旁白使它成為五部作品中最特殊的存在。雖然所使用的並不是一般觀眾能夠理解的語言,使得多數人對劇情仍只能靠影像來理解。導演的赤子之心讓這部作品充滿了濃濃的童趣──不只是因著童畫風格的人物造型和場景,而是對於父親形象的塑造上,與孩子眼中的偉大形象一致。
《彩虹的缺口》可能是入圍作品中最深沉的作品,其中不少意象的鋪排都殘酷地令人不忍卒睹。比如在疑似天堂的地方赫然出現代表惡魔的蛇,或是主角兔子在四處漂流時所遭遇的對待,都可看見故事設計的用心。不過,在動畫的執行上則有些明顯合作的瑕疵,不免令人扼腕。
動畫電影的創作,導演所能主導的部分其實較諸一般電影是更高的。從角色外貌的高矮胖瘦到最終影片整體呈現的結果,理論上都可以完全依照創作者的意念執行。或許因為如此,在小型製作下的參賽影片更容易出現因為個人專長與著重的事務不同,而有顧此失彼的現象。也許要出現更好的作品,必須要更大型的團隊,群策群力才能互補每個人的不足,這點在金穗獎的參賽作品不能被苛求,但這些入圍影片背後的優秀團隊未來若有勇氣與毅力持續向這條路走下去,出現更多高度分工與合作的團隊,將是我個人對台灣動畫電影最深的期許。
相關放映資訊:(詳細說明請參見本篇)
5/09(六) 18:30 誠品信義店:五部聯映 + 映後座談
5/15(五) 20:30 誠品信義店:五部聯映
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reke的金正碎碎唸」系列前言
即日起,本部落格將不定期的推出「reke的金正碎碎唸」單元,是針對第31屆金穗獎的35部入圍作品的系列書寫。首先推出的第一篇,將會是就我工作相關的「最佳動畫」五部入圍作品做一概述。未來也會儘可能地向讀者們介紹這些台灣電影的新活力。
關於金穗獎的更多消息,可以參考第31屆金穗獎的官方部落格、部落格達人獎專屬部落格以及官方網站。
之所以命名為「金正穗穗唸」,主要是不才格主雖然接下了本屆金穗獎部落格達人獎評審的重責大任,然而我所有關於電影的書寫,都只能說是個人最主觀的好惡。實在不敢因為頂了會外獎性質的評審名頭,就讓個人有限的眼光置入這個行之有年,獎勵過諸多優秀台灣新電影工作者的活動中。所以,這系列的書寫就當作是我個人的碎碎唸吧!
最後,希望看到文章的朋友,除了不吝批評指教以外,也要多多支持金穗獎!
「金正穗穗唸」系列放映資訊說明:
1.由於各場次均有多部作品聯合放映,每篇文章後面只列出文中有評述的影片片名,另以括號表示該場其他文中未提及的作品數量。例如該場放映《海角七號》+《囧男孩》,而文中僅提及《囧》,則寫為「囧男孩(+1)」
2.所有場次資訊悉依31屆金穗獎官方網站所提供下載的場次表發佈。如有更動或誤植情事,請以官方公告為準。場次表下載連結在此。
3.放映地點說明
誠品信義店: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檢視較大的地圖
電影資料館: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7號
檢視較大的地圖
關於金穗獎的更多消息,可以參考第31屆金穗獎的官方部落格、部落格達人獎專屬部落格以及官方網站。
之所以命名為「金正穗穗唸」,主要是不才格主雖然接下了本屆金穗獎部落格達人獎評審的重責大任,然而我所有關於電影的書寫,都只能說是個人最主觀的好惡。實在不敢因為頂了會外獎性質的評審名頭,就讓個人有限的眼光置入這個行之有年,獎勵過諸多優秀台灣新電影工作者的活動中。所以,這系列的書寫就當作是我個人的碎碎唸吧!
最後,希望看到文章的朋友,除了不吝批評指教以外,也要多多支持金穗獎!
「金正穗穗唸」系列放映資訊說明:
1.由於各場次均有多部作品聯合放映,每篇文章後面只列出文中有評述的影片片名,另以括號表示該場其他文中未提及的作品數量。例如該場放映《海角七號》+《囧男孩》,而文中僅提及《囧》,則寫為「囧男孩(+1)」
2.所有場次資訊悉依31屆金穗獎官方網站所提供下載的場次表發佈。如有更動或誤植情事,請以官方公告為準。場次表下載連結在此。
3.放映地點說明
誠品信義店: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檢視較大的地圖
電影資料館: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7號
檢視較大的地圖
2009年3月3日 星期二
誠實的超脫─評《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
 應該說很幸運地,《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跟台灣觀眾見面的日期,正好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後。而甫奪得最佳外語片獎項的氣勢,也讓這個不太討好的主題,居然出現了滿座的人潮。能有更多的人接觸到這部電影,那麼它其中所展現對於生命的思考與尊重,也就能在這個社會播下更多的種子。
應該說很幸運地,《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跟台灣觀眾見面的日期,正好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後。而甫奪得最佳外語片獎項的氣勢,也讓這個不太討好的主題,居然出現了滿座的人潮。能有更多的人接觸到這部電影,那麼它其中所展現對於生命的思考與尊重,也就能在這個社會播下更多的種子。電影跟隨著因為失業、夢想破碎的小林大悟(本木雅弘飾),一足踏入納棺師的世界。而觀眾跟著電影鏡頭,也在短短的時間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態。有些往生者有較完整的支線交代他們在世時的故事;卻有更多的往生者,只有幾個鏡頭的時間,只有一項親人告別時的特殊儀式,可以在一個陌生人──納棺師,或是電影觀眾──的心裡留下印象。在影像不斷地堆疊著每一次死別的場面時,這些往生者背後龐大的生命故事,也逐漸的累積起動人的能量。
M而,若只是強調死別的不捨與苦痛,電影終將只淪為灑狗血騙眼淚的庸俗品。事實上本片透過不少前後呼應、反覆出現的橋段,展現了死亡除了別離以外的面向。而且,其探討的內容遠超過宗教的範疇。除了去追問並試圖描繪死亡的意義外,更讓死亡變成往生者與其在世親友之間情感的總結算。
在電影裡,往生者對於納棺師,無論生前是否相識,然而在為大體化妝的時刻,卻是沒有任何祕密的。無論是性別認同問題、家庭教養問題,還是與親人間的種種約定,都必須在這一刻有意或無意地攤在納棺師的面前。這些祕密對於納棺師而言,更不是無關緊要的故事,而是他必須據以判斷如何為死者塗抹容顏的依據。這些納棺師的苦心能否使往生者在人生的最後一程真的了無遺憾,恐怕無人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對於還在世的親友而言,那就是往生者在被蓋棺論定之前,最真誠且最堅定的告白──不容置疑,更無法再透過情感的壓力屈服其意念。若好似某些人所認為的,死亡是種超脫,那麼《送行者》為納棺師工作所塑造的意義,就是在幫助生命實踐這樣的超脫與自由。
從這個觀點回頭來看小林大悟本身的故事,無疑地也扣著超脫、自由的母題在進行。刻本先將這個角色設定為總是把祕密往心裡藏的性格,因為害怕他人的不諒解,所以總是選擇獨自面對。然而,這些祕密總算是一項一項地獲得解脫:在音樂上,演奏不再是一項吃飯的工具、不再是應付父親權威的表演,而是發自內心的感懷;在父親缺席帶給他的傷害上,他也在窺見父親最後的祕密時得到釋放,讓童年的遺憾不再造成沉重的怨懟。在這個角色身上,觀眾可以很樂觀的看見,不是所有的自由與超脫,都只能等到死去的時刻才得以體現。如果面對死亡、親近死亡,可以讓人在此生能夠確定的當下就獲得超脫,那麼這部哀戚氛圍濃厚的電影,其實還是充滿正面的希望與陽光的。
2009年2月17日 星期二
平庸的困局─評《真愛旅程》

李奧納多迪卡皮歐 (Leonardo Dicaprio) 與凱特溫絲蕾(Kate Winslet) 在《鐵達尼號》(Titanic)的合作,是去追求一個浪漫而帶有些遺憾的自由美國夢;怎料十年之後,兩人再次攜手的《真愛旅程》(Revolutionary Road),卻是要從現實而殘酷的美國世界逃離,卻又因為自囚而走不開的悲劇。於是,這對銀幕情侶的再度合作,除了純粹的電影宣傳噱頭之外,還多了幾分影像對話的趣味。就像是法蘭克(Frank)與艾波(April)初遇的那場戲,法蘭克那人窮志高的模樣著實讓我心中傑克(Jack)的影子又浮現了出來。幸好,故事中嚴肅而龐大的命題,而李奧納多與凱特十年洗鍊下來的演出,也不復見當年青澀。因此鐵達尼的陰影在其他鏡頭內都更不復見。
法蘭克與艾波這兩個角色在電影裡的互動,在開場沒有多久就透露出了端倪:兩人的溝通總是陷入困境,並且總是以尖銳的、激烈的爭執做為最終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對話走入死胡同,其中揭示了夫妻相處間各種兩難的問題:要求多變化的情趣經營、亦或無味的安全感;要事事溝通共享,亦或是各自保留私人情緒空間。這些性格上的差異,在電影當中看似做了太過誇張的表演,然而實際上,那只是外在的社會環境壓力催化的結果。威勒夫婦對於現在居處是去或是留,周遭人事一面以金錢、地位與性加以誘惑,一面以死氣沉沉的環境、工作與社會輿論加以驅趕。矛盾和對立在這樣難以逃離的環境下,才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性。
婚姻中的問題、人與社會環境的磨擦,這兩條主線在電影中相互糾纏、相互突顯。這樣的故事特色使得《真愛旅程》中對夫妻生活的描寫,有別於其他探討此類問題的電影。比方說在描述艾波的不耐情緒時,導演並沒有讓這個角色花太多的時間在表演家事的無聊與厭煩;而一般婦女教子的辛苦,在電影中幾乎未曾呈現,甚至兩人的孩子幾乎只有在全身到遠景的鏡頭出現,也幾乎未成為畫面構圖的焦點。家事的枯燥與教子的壓力,這是在描寫傳統社會婦女被壓抑的處境時最好用的工具,在這部電影裡卻被全面揚棄,這對於觀眾的理解勢必成為一種挑戰。如果不能夠以同情的視角審視艾波對與夢想的渴望,那麼就會難免陷入與法蘭克相似的處境──在眼裡只看見一個歇斯底里的、瘋子式的存在。反過來說,如果能夠意識到本片在處理婚姻問題上的特殊性,那麼對於艾波與法蘭克的衝突才能夠得到充分的理解。
正如同原著小說和電影的英文片名所揭示的,這個故事其實與革命脫離不了關聯。革命這個帶有些左派浪漫的詞彙,使我們必須去檢視電影中描寫的階級與性別問題。在階級的層面,透過法蘭克上班過程──千篇一律的身影朝著鏡頭淹來──已經不著痕跡地控訴了資本主義之下,被扼殺的個人創造力。這樣的控訴一度讓艾波搬家遠行的要求站穩了正當性,也讓法蘭克的猶疑顯得畏縮、懦弱。然而,資本主義神話最拿手的把戲並不僅僅是製造出一批又一批乖巧的上班族,而是替這些乖巧的臉孔製造少數的夢想,使其心甘情願地沉溺在有朝一日能夠自我實現的幻夢中。法蘭克的角色在造夢的戲碼裡面扮演了雙重的身分,一方面他就是那個逐夢成功的榜樣,是其他眾人幻夢中的理想形象;而另一方面他也是被欺騙的對象,他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情況下,投入了一個幾乎失去思考的必要,只需要無意義的胡鬧的工作中。眾人連同法蘭克自己都稱羨的地位與財富,輕而易舉地收編了對革命的熱情。而法蘭克將追逐自己幻影的過程,誤認為是自我實現,更讓他無法自拔地踏入悲劇的泥淖中。
對比於法蘭克的迷失,艾波在對於自我實現的道路上清晰得多。然而,她的女性身分卻讓這條路遙不可及。雖然在表面上,家庭充裕的經濟讓她得以省去教子的心力;而法蘭克相對於旁人閒言,對女人賺錢養家的開明態度似乎也支持了其追逐夢想的空間。然而,無法控制的生育能力,讓她必須承受身體對於心靈的背叛;而女性情緒化、感情用事的刻板印象,在法蘭克要否決她的意見正當性時,又變成最好的藉口。然而更令旁觀者替艾波感到難堪的地方或許是,當艾波踏出試圖控制自己的第一步後,總是招來更大的、來自於自身的毁滅。同時身為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艾波,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與同時身為騙子與被欺騙者的丈夫法蘭克相互呼應;然而事實上,艾波面臨的矛盾比起法蘭克的更顯得血腥而且赤裸。她無法如同面對愚蠢的頂頭上司那般,用暗度戲謔之意的工作成果來獲取阿Q式的精神勝利。以電影中的性愛為喻,法蘭克的男性身分使他極易從性愛中將庸俗的憂慮短暫發洩,而艾波的女性身分在性愛後,卻無疑地讓庸俗在體內著了床,成為既屬於她而又不屬於她的一部分,並且還能感受到他的成長。艾波對於被庸俗吞噬的焦慮之所以倍於法蘭克,性別的差異無疑是其中關鍵的要素。
無論從哪一個面向切入,這部由重重隱喻和象徵所織就的電影,總是可以找到一條豐富的線索,引領觀眾深入的思索人生困境。在這個平凡人充斥的世界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對於這樣的命題感到心有戚戚。然而導演在最後一幕揭諸螢幕上的解脫之道,或許有些叫人感到灰心絕望。艾波的血祭儀式終究未能撼動革命解放之路的天真與遙不可及,而若觀影者在接受了這樣的震撼之餘,在面對這種不見、不聞的灑脫之時,究竟該嘆服其偉大的人生智慧,亦或抗議其腐蝕鬥志的鴕鳥心態?或許,這個見仁見智的選擇題,會讓這部電影更加的耐人尋味。
2009年1月12日 星期一
滿口外行話─評《彈道》
 遙想當年,台灣的周人蔘案、宋七力事件、全民計程車事件,在香港被大鍋炒在一塊兒,拍成《黑金》(或名:《情義之西西里島》);後來,在台灣發生女議員遭到偷拍性愛光碟事件,又被香港的電影圈拿去藉題發揮成《偷窺無罪》。這一次,在台灣挑動敏感政治神經的三一九槍擊案,又被拍成了《彈道》。香港對於台灣社會事件的關注,在電影世界裡儼然自成一脈。這些社會事件在香港編劇的眼中,本身似乎就有足夠的戲劇張力,因此無論是先前的《黑》、《偷》二片,還是最新出產的《彈道》,都毫不掩飾其取材的來源,以其情節和真實事件、角色和事件當事人之間高度的雷同,都已經超過「參考」的界線,來到「影射」的範圍了。
遙想當年,台灣的周人蔘案、宋七力事件、全民計程車事件,在香港被大鍋炒在一塊兒,拍成《黑金》(或名:《情義之西西里島》);後來,在台灣發生女議員遭到偷拍性愛光碟事件,又被香港的電影圈拿去藉題發揮成《偷窺無罪》。這一次,在台灣挑動敏感政治神經的三一九槍擊案,又被拍成了《彈道》。香港對於台灣社會事件的關注,在電影世界裡儼然自成一脈。這些社會事件在香港編劇的眼中,本身似乎就有足夠的戲劇張力,因此無論是先前的《黑》、《偷》二片,還是最新出產的《彈道》,都毫不掩飾其取材的來源,以其情節和真實事件、角色和事件當事人之間高度的雷同,都已經超過「參考」的界線,來到「影射」的範圍了。香港電影人如此愛好台灣的時事題材,相較之下,台灣電影人,尤其實許多自許本土情懷的電影導演,他們的影像和台灣社會的互動,似乎比較偏好「遲到」的對話。他們的鏡中愛好追憶過去的台灣,喜歡沉重的歷史反思或惆悵的年少追憶。侯孝賢、吳念真一輩的導演在日治台灣、二二八事件上的遲到,倒還能從早年根本沒有容許拍攝此類題材的空間來解釋,然而近年台灣電影卻依舊呈現這樣的性格。例如剛剛遠去不久的2008年,《九降風》談的是12年前的黑鷹事件、《一八九五》與《海角七號》分別標識了日治時期的開始與結束。有興趣處理當下社會的劇情片付之闕如,院線只有兩部不太純粹的紀錄片《星光傳奇》與《態度》勉強算是跟上了時代話題。
港台兩地電影圈的奇特對比,或許可以當作由電影切入社會、文化觀察的好題目,然而限於其他資料的不足,容我在這裡點到為止。接下來重心還是要回來談談《彈道》這部電影本身。
《彈道》上映以來,無論在港在台,觀眾的反應評價皆不如預期。足見電影話題性雖然足夠,然而若無好的內容支撐,再好的題材都只能被辜負。《彈道》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編劇未能妥善掩藏自身經驗的不足,於是將一部詭譎的政治陰謀寫得膚淺不已、破綻百出,絲毫感覺不出背後懸疑、尖銳的權謀計算,只剩下鬆散的新聞事件串連。
應該是為了讓這個政治事件看起來較具有陰謀性,所以在眾說紛紜的三一九槍擊案說法中,《彈道》採用了深藍支持者最願意相信的版本:一開始就將這齣槍擊案定調為「自導自演」的大戲。這樣的作法其實正弄巧成拙,將事件真正引人疑竇的地方都消耗殆盡。事實上這個案件之所以有話題性,有諸多揣測,正是因為開槍動機有各種可能,致使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電影卻大喇喇地順敘出計劃過程,又沒有半點心思去經營執意追查真相的基層呆警察如何被誤導、如何視破其技倆,那麼事件的陰謀性就先去了一半兒。接下來,基層警察與府院高層間的對決又過分直來直往,張國柱如何精湛的演出,都無法說服他人,一個台詞不會拐彎、對「非自己心腹」的醫院院長、警察主管下達指令而完全不掩飾動機的人,怎麼可能是老謀深算,為主子策劃出逆轉戰役的高明策士。
在操盤主謀被寫得只有狠勁、沒什麼腦筋的情況下,為了維護這個角色的說服力,編劇更進一步將旁人寫成全然的世道白痴。當到醫院院長的人,會在大長官下達清場令時仍叨叨絮絮的掛念「這是我們醫院的責任」;上頭的大老闆,除了罵人與說一些「要想辦法贏回來」的廢話之外,絲毫看不出有何在政治鬥爭中勝出、爬到上位的才能;至於負責接招的泛藍陣營方,謀士是一派荒亂、主子是隨口出策,連像樣的選務決策機制都不可見。這些角色雖然大部分都無足輕重,但是塑造的隨便讓電影顯得幼稚可笑,張力也在此間被消磨得一乾二淨。
的確,編劇的工作只是編劇,他未必參與過選舉,未必混過黑幫。然而編劇工作的價值,就是能夠應用推理、想像,讓門外漢也能透過少數的資料,精確地揣摩出合乎角色身分的專業口吻──或者說,至少能騙倒多數觀眾的專業口吻。若是外行人說外行話,要撥弄觀眾的心弦,恐怕是難上加難了。
2008年12月22日 星期一
既無真情,何來好戲?─評《梅蘭芳》
 陳凱歌懂得讓邱如白對著少年時期的梅蘭芳,侃侃而談真情在戲中的重要性。然而諷刺的是,《梅蘭芳》就紮紮實實地敗在這個「真」字上頭。為了塑造梅蘭芳的高潔氣質,劇本真將其所做所為寫得一塵不染,讓卸下了臉譜的梅蘭芳,依舊好似畫著一副花臉般,叫人看著如隔靴搔癢,難以進入這位一代名伶的生命中。
陳凱歌懂得讓邱如白對著少年時期的梅蘭芳,侃侃而談真情在戲中的重要性。然而諷刺的是,《梅蘭芳》就紮紮實實地敗在這個「真」字上頭。為了塑造梅蘭芳的高潔氣質,劇本真將其所做所為寫得一塵不染,讓卸下了臉譜的梅蘭芳,依舊好似畫著一副花臉般,叫人看著如隔靴搔癢,難以進入這位一代名伶的生命中。就算不重提《霸王別姬》的經典地位,單就《梅蘭芳》的前段來看,或許誰都不相信陳凱歌對於京劇題材的掌握無能為力。少年梅蘭芳在鏡頭底下,將桀傲不馴的叛逆,化在陰柔身段與壓抑的情緒表現裡;與十三燕之間的對台戲,其中展現兩代壓抑的情感,以及時代舞台的殘酷,直教人動魄驚心。鬥戲過程中,梅蘭芳這方多用觀眾的視角,緊跟著台上那個「她」的一顰一笑;而十三燕這頭,即使剪接已經明示戲迷的背棄,鏡頭仍然小心翼翼的切在舞台的前緣,讓電影觀眾一同體會了十三燕那忍受寂寞,堅持唱完最後一個身段的辛酸。
少年梅蘭芳的故事,道盡戲子用台下的血淚鑄成台前風光的矛盾、掙扎;也在黃馬褂和洋留學生的對照之間,展現了那個巨變時代的氛圍。這個段落中無論梅蘭芳也好、十三燕也罷,兩人在戲台下對白的口條仍然維持著極戲劇的怪腔,然而即便如此,卻未嘗使人感到一絲的矯情。每個角色的表演恰如其分,運鏡、對白與事件橋段亦是飽滿豐富,大有挽回陳凱歌盛名的氣勢。
不料進入中段以後,黎明與章子怡兩大主角翩然出場,電影卻也每下遇況。我無意將原因歸咎於兩人的演技,因為憑著劇本對二人調情的有氣無力,恐怕是難以靠著演員個人的能力去彌補的。
如果說梅蘭芳與十三燕間的情誼,可以敷衍成時代更迭的悲壯輓歌;那麼蘭孟之戀,同樣也可以加油添醋,賦予更多人性的掙扎。兩人台上、台下間的性別倒置;公眾人物面對社會輿論加諸身上的枷鎖;甚至是藝術成就與私人情感間的取捨衝突──每一項鋪排起來都可以劇力萬鈞,揪起觀眾的心緒。然而《梅蘭芳》裡卻是樣樣都沾上了邊,樣樣也只沾上了邊。最可笑的莫過於那場意在棒打鴛鴦的槍擊戲碼,持槍人才泣訴完男身女心導致精神錯亂的折磨,梅蘭芳的回答台詞竟是如此無關痛癢、文不對題、答非所問。而有「冬皇」之稱,以女扮男聞名的孟小冬,在面對這樣的質問時卻毫無表演空間,一個好端端的重要角色就被編導擱到了一邊。最偏激的戲卻搞出了最散亂、最無厘頭的收尾,著實浪費了這段愛情的特殊性。
 且莫說這段愛情背後多少象徵、衝突可以發揮。就算退一步將它當成簡單的羅曼史看看,電影中也鋪不出那熱切的愛戀。孟小冬何以離不開梅蘭芳?梅蘭芳何以在孟小冬處可以消解孤單?台詞雖然寫得明白,然而故事卻說得不明不白。即使梅蘭芳對情感壓抑、內斂,電影仍然可以用鏡頭、用意象的推砌,去代替角色說出他們不敢說出的情感。然而陳凱歌卻寧可用了許多心血,花在福芝芳與孟小冬的女人對話上。總而言之,青年時代的梅蘭芳,就在這蜻蜓點水、一再離題的混亂故事裡,被平平淡淡地帶過了。
且莫說這段愛情背後多少象徵、衝突可以發揮。就算退一步將它當成簡單的羅曼史看看,電影中也鋪不出那熱切的愛戀。孟小冬何以離不開梅蘭芳?梅蘭芳何以在孟小冬處可以消解孤單?台詞雖然寫得明白,然而故事卻說得不明不白。即使梅蘭芳對情感壓抑、內斂,電影仍然可以用鏡頭、用意象的推砌,去代替角色說出他們不敢說出的情感。然而陳凱歌卻寧可用了許多心血,花在福芝芳與孟小冬的女人對話上。總而言之,青年時代的梅蘭芳,就在這蜻蜓點水、一再離題的混亂故事裡,被平平淡淡地帶過了。為什麼梅、孟之戀會寫得如此尷尬?我的臆測是,這段戀情算是婚外之情,拍得輕描淡寫,都已經喚出了元配梅芝芳的苦情。若要拍得濃了,恐怕終究有損梅蘭芳之格。
 至於進入日軍侵華時期後,真叫人搞不明白電影名為《梅蘭芳》還是《邱如白》了。藝術是否具有獨立的價值?以藝術的犧牲換取政治上、民族上的認同是否值得?這些值得反覆思辯的議題,竟然無擱到邱如白的身上。至於梅蘭芳──為了展現其高潔性格,電影竟擱下了他對戲劇的執著,全力刻畫他不屈的風骨。要將梅蘭芳寫成愛國志士並無不可,然而脫離了京劇而單寫其愛國精神,如此終失了一代名伶的特殊性。即使梅蘭芳在抗戰中拒不公演,仍然有許多手法能端出京劇戲碼來,再透過戲中戲展現那些複雜的掙扎。可惜梅蘭芳面對戲與民族情感間的取捨,一派地無動於衷,大大削弱了這個角色的力量。
至於進入日軍侵華時期後,真叫人搞不明白電影名為《梅蘭芳》還是《邱如白》了。藝術是否具有獨立的價值?以藝術的犧牲換取政治上、民族上的認同是否值得?這些值得反覆思辯的議題,竟然無擱到邱如白的身上。至於梅蘭芳──為了展現其高潔性格,電影竟擱下了他對戲劇的執著,全力刻畫他不屈的風骨。要將梅蘭芳寫成愛國志士並無不可,然而脫離了京劇而單寫其愛國精神,如此終失了一代名伶的特殊性。即使梅蘭芳在抗戰中拒不公演,仍然有許多手法能端出京劇戲碼來,再透過戲中戲展現那些複雜的掙扎。可惜梅蘭芳面對戲與民族情感間的取捨,一派地無動於衷,大大削弱了這個角色的力量。總括來說,電影後半的梅蘭芳過於高貴。一切人性中的陰暗皆被抿除,終於將這個角色搞成了神像般的存在──高迥在上,卻了無生命。不若第一段,梅蘭芳擊垮其所敬愛的十三燕,甚至令老人家抑鬱而終那般,具有矛盾、高潮的衝擊。離了人性、離了真實的情感,就無戲可做了。邱如白的信箋言猶在耳,卻成了對《梅蘭芳》最大的諷刺。陳凱歌何時能再建立《霸王別姬》的經典地位?恐怕影迷也說不得準了。
2008年12月2日 星期二
不缺席的男人─評《女人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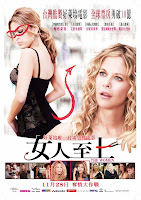 打出了聳動的宣傳,將電影中所有男人的身影全都趕出了鏡外,這是《女人至上》(The Women)大膽的嘗試。然而,仔細審視劇情的內容之後,卻發現電影本身其實並不那麼激進。我們看到瑪莉海恩斯(Mary Haines,梅格萊恩 Meg Ryan 飾)在片中為了處理先生的外遇危機而焦頭爛額;又看到希微佛勒(Sylvia Fowler,安娜特班寧 Annette Bening飾)在與男性上司的角力中載浮載沉;還有伊蒂克萊(Edie Cohen,戴博拉梅西 Debra Messing飾)為了生出男孩而不斷努力地懷胎。
打出了聳動的宣傳,將電影中所有男人的身影全都趕出了鏡外,這是《女人至上》(The Women)大膽的嘗試。然而,仔細審視劇情的內容之後,卻發現電影本身其實並不那麼激進。我們看到瑪莉海恩斯(Mary Haines,梅格萊恩 Meg Ryan 飾)在片中為了處理先生的外遇危機而焦頭爛額;又看到希微佛勒(Sylvia Fowler,安娜特班寧 Annette Bening飾)在與男性上司的角力中載浮載沉;還有伊蒂克萊(Edie Cohen,戴博拉梅西 Debra Messing飾)為了生出男孩而不斷努力地懷胎。如何處理男人、維護傳統家庭的價值,讓這部電影呈現了一種尷尬的局面──鏡頭裡全部都是女人的身影,但是鏡頭外的男人依舊主導著大局。每個重要角色的心境、決策,幾乎都是由男人在推動,而她們卻鮮少真的完全憤恨式的拒男人於千里之外。這種以男性推動劇情的思考,同時也大大削弱了艾麗絲費雪(Alex Fisher,潔達蘋姬 Jada Pinkett Smith飾)這個角色的生命。她的女同志身分在片中幾乎沒有產生任何意義,即使去掉絲毫不影響電影的劇情。
誠然,在面對真實世界的男女互動時,是無法也不應該完全跟男人隔離的,但是電影畢竟在表面上先站上了光譜上的極端,其內容未能更尖酸刻薄地朝著男人抗議,就顯得這激烈的作為只是一種商業噱頭。編導既然聯手將所有男性生物踢出了鏡外,何以要讓兩個男人同時進入女人的圈子來當做美好的結局?這樣的矛盾固然並不是不能透過劇情的發展過程予以彌補,然而整部電影裡,說的都是女人間的友情、情親和戰爭,對於男女之間的歧異並沒有太多發揮。所以,男人在電影裡到底是存在還是缺席,就成了本片令人疑惑的所在。

不過,撇開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女人至上》在對於女性生命處境的描寫上,仍然有其可圈可點之處。比如在面對時尚──一套綁架女人,卻同時宣稱滿足女人天性的商業機制──的態度上,《女人至上》的譏諷就顯得不落痕跡。當伊蒂的女兒高喊她討厭百貨公司,卻遭到希薇的訓示時,正像是被孩子喊破真相,卻仍執迷不悟的國王一樣,嚴厲地反應了社會將女性由一個「女孩」引導、塑造成為一個「女人」的過程中,出現了什麼樣的荒謬景象。至於瑪莉被父親逐出家族事業,到三代母女攜手完成的服裝秀,則高明地反抗了男性宰制女性時尚的怪異現象;比起由電視轉戰大螢幕的《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毫無保留地擁抱時尚,《女人至上》對於女性的被物化顯然還抱有相當程度的警覺心。
至於情感的部分,女人間的友情,電影中並未出現太多突破,背叛與諒解的衝突都可以看到許多其他作品的影子;然而對於上下兩代親情的描寫,《女人至上》卻有著令人可喜的細膩。對比好萊塢慣常出現親子間攤牌懇談的情節,電影中卻充分將女人間特有的溝通的模式引入親子的對話中。母女兩人大費周章的透過第三人的傳話完成交心,同時也解開了好友間的誤會心結。這個橋段讓女人間的私密群體中,除了橫向的朋友關係,又多出了縱向的母女關係,十分契合女人之間那永遠另男人猜到頭痛的複雜交誼模式。
給與男性一個尊榮的虛位、對於女性情感細微的描寫,加上輕鬆幽默的笑料。《女人至上》雖然稱不上是真正女性本位的電影,但或許是讓男人無需升起武裝的女性電影。如果說《慾望城市》要與姊妹淘一同品嚐的話,《女人至上》或許正適合牽著男人的領帶,把他們一並拉進戲院吧!
2008年11月16日 星期日
平靜的洶湧─評《渺渺》
 小璦(張榕容飾)說,她喜歡做蛋糕的原因,是因為蛋糕帶給人們幸福的感覺。然而,這個代表幸福的蛋糕終於是碎了,在奮力的追尋與無力的失落之中碎了。而在那不忍卒睹的悲傷之中,我們卻仍需要品嚐斷垣殘片裡僅存的甜美,並且為了這份美味強顏歡笑。
小璦(張榕容飾)說,她喜歡做蛋糕的原因,是因為蛋糕帶給人們幸福的感覺。然而,這個代表幸福的蛋糕終於是碎了,在奮力的追尋與無力的失落之中碎了。而在那不忍卒睹的悲傷之中,我們卻仍需要品嚐斷垣殘片裡僅存的甜美,並且為了這份美味強顏歡笑。《渺渺》的身上有許多台灣近年電影的血液:小品、青春、文藝、同志戀情,同時在敘事節奏的拿捏上稍欠起伏。但是,由於精確又平易的象徵,以及對主題深刻的思考,我認為這部電影的可看性仍是相當高的。尤其當隨著人生歷練的增長,在生命中逐漸累積許多不完美的遺憾回憶時,更能夠看見《渺渺》在青春美麗的外貌之下,埋藏著多麼深刻的嘆息和悲哀。
之所以強調《渺渺》意涵的深刻,在於我不認為這個故事的動人之處,只在於建構一種青春年華的懐舊氛圍,並且訴諸電影反映的世代的共同默契,讓閱讀過程中不得不感受創作者心中那深深的排他性;相反地,《渺渺》中討論的命題是跨越身分與年齡的:關於愛、幸福、記憶三者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糾葛。換句話說,在調性上,《渺渺》與今年稍早時頗受好評的《九降風》並不相同,反而接近去年的《沉睡的青春》──我一直認為,較之前者容易受到世代的局限,後者才有更多可以閱讀、討論,甚至是再創作的可能性。
 電影裡出現了不少看似思想矛盾的劇情:對走不出初戀記憶的人,它可以表現出同情甚至欽羡;而另一方面,卻又語帶雙關的要人們「忘掉他的一切、忘掉他的長相」,才能去品嚐幸福的美味。事實上,與其說這樣的歧異是電影本身的矛盾,倒不如說是一段精彩的辯證。畢竟我們對於逝去的幸福,所存著的心理就是會如此的矛盾──一會兒想牢牢留住所有曾經的美好,在悲傷中暗自緬懷;一會兒又想狠下心來消除一切的記憶,讓遺忘與空白麻醉沉痛的心扉。若是曾經在忘與不忘之間,任著肉做的心承受來回拉鋸子的折磨,那麼一定能體會到在《渺渺》看似平淡的劇情下,其實有多麼波濤洶湧的情感衝突。
電影裡出現了不少看似思想矛盾的劇情:對走不出初戀記憶的人,它可以表現出同情甚至欽羡;而另一方面,卻又語帶雙關的要人們「忘掉他的一切、忘掉他的長相」,才能去品嚐幸福的美味。事實上,與其說這樣的歧異是電影本身的矛盾,倒不如說是一段精彩的辯證。畢竟我們對於逝去的幸福,所存著的心理就是會如此的矛盾──一會兒想牢牢留住所有曾經的美好,在悲傷中暗自緬懷;一會兒又想狠下心來消除一切的記憶,讓遺忘與空白麻醉沉痛的心扉。若是曾經在忘與不忘之間,任著肉做的心承受來回拉鋸子的折磨,那麼一定能體會到在《渺渺》看似平淡的劇情下,其實有多麼波濤洶湧的情感衝突。在這個短小的故事裡,承載了太多的不完美:殘缺的家庭、破碎的蛋糕、需要拼揍的歌名,甚至連故事本身都在結構上呼應這種殘缺的美感,所以才將唱片行老闆陳飛(范植偉飾)的故事拆成了好多斷片,不斷在渺渺與小璦的故事中插敘著。透過結構與劇情的呼應,電影中其實一再暗示了生命中必定要面臨的殘酷事實:缺憾實在太多,而完美似乎並不存在。相較起小璦、渺渺所經歷的,從來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的愛情,這個對於生命所寫下的殘忍註腳,才是更值得一慟的所在。
我極願意將《渺渺》推薦給每一個人欣賞,因為它不只是一部純愛電影,在那些青澀的情感背後,有編導對於人生的洞見。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