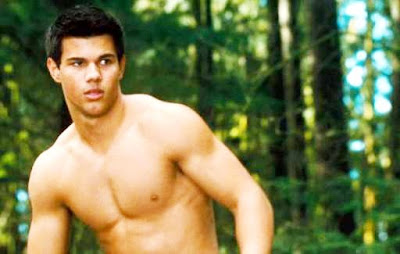《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被目為一部經典的成人童話,透過瘋狂的情節與對白,大大嘲諷了成人世界的乏味。但是回過頭來說,儘管許許多多的成人在回首孩堤往事的時候,都會對這部童話發出會心的苦笑,但令人遺憾的是,若我們真的回到童年的赤子之心,世界恐怕也不會變得更好。那些天真的、瘋狂的、有創意的、有活力的仙境,其實是躲在成人建立的秩序環境下奢侈的縱容。
《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被目為一部經典的成人童話,透過瘋狂的情節與對白,大大嘲諷了成人世界的乏味。但是回過頭來說,儘管許許多多的成人在回首孩堤往事的時候,都會對這部童話發出會心的苦笑,但令人遺憾的是,若我們真的回到童年的赤子之心,世界恐怕也不會變得更好。那些天真的、瘋狂的、有創意的、有活力的仙境,其實是躲在成人建立的秩序環境下奢侈的縱容。上述感嘆的文字看似引言,其實應該是結論,是看完提姆波頓(Tim Burton)的《魔境夢遊》(Alice in Wonderland) 之後所激起的思索。這位向來以獨特美學著稱的導演,在迪士尼旗下的作品看似溫和了許多,過於刺激、詭譎的對白不復出現,但是整體故事的架構來看,依然顯得十分蒼涼。
《魔境夢遊》裡的愛麗絲(Alice,Mia Wasikowska 飾)從小女孩長成了大女孩,但對於成人的世界依然格格不入。在開場短短的求婚場合裡,電影讓愛麗絲的一言一行都與周遭的親朋好友間產生極嚴重的對立,於是,夢境就成為她逃脫的出口。然而,與原著《愛麗絲夢遊仙境》精神大為不同的地方是,這個「仙境」對於愛麗絲而言,不再是一個全新的、虛幻的、跳脫的、瘋狂的以及值得探索的地方。愛麗絲雖然透過夢境逃離了人世間的秩序,但是卻必須在夢境裡承擔眾人期待的救世主身份,去回復這個世界中的秩序。換句話說,整串任務的成功,對於愛麗絲來言就算是一種失敗。即使愛麗絲在倔強的性格驅使下,她也曾經試圖拒絕往命運走去,不過種種動作反而使她誤打誤撞地迎合了命運安排的結局。
儘管電影裡不斷反覆地問著原著中的無意義問題:「鳥鴉為什麼長得像書桌」 (Why is a raven like a writing-desk),但實際上,《魔境夢遊》卻離開去意義化的精神甚遠。整個故事的架構四平八穩,甚至直白不諱地鋪陳一個陳腔濫調式的屠龍故事。會有這樣的裂縫,我倒不認為是提姆波頓對於原著的誤讀。原因在於,電影並不是在描述夢想的建立,而是在演繹夢境的終結。在愛麗絲於夢境中冒險的過程裡,電影不斷對於她甦醒之後,夢境的存在性進行辯證。而從她甦醒後戳破他人的幻夢,又果決、斷然地投入現實世界,大談商業帝國的版圖擴張,我們固然看見了愛麗絲瘋狂的勇氣,但也意識到失去成人的羽翼之後,她的瘋狂夢想,也只能夠在「現實」層面中發展的困窘。

當然,單從觀察到故事結構中透出的矛盾後,就將《魔境夢遊》視為對《愛麗絲夢遊仙境》嘲弄而非致敬,難免顯得附會,所以我還要從電影中指出幾個地方,暗暗埋藏了諸多自我顛覆的詭異安排。例如一派良善天真的白皇后(The White Queen,安海瑟威 Anne Hathaway 飾)在調配藥劑時流露出的血腥氛圍、在處罰姊妹時又顯得偽善;又如瘋狂帽客(The Mad Hatter,強尼戴普 Johnny Deep 飾)鼓動民心的氣勢、對於自己存在的重視,與對愛麗絲的離去的牽絆,也都暴露其「瘋狂」似乎只是政治氣氛不佳時,賴以苟活的包裝。而夢境中的人物、場景與現實生活的對應,更讓心理學的嚴肅理論替夢境中天馬行空的程度打上幾分折扣。
這些現象不約而同地將電影中的夢境導向虛假時,原先看似矛盾的點反而產生了一致性,指明《魔境夢遊》對於赤子之心的思考,並不是表面上看來那麼淺白。看來,當觀眾習於期待提姆波頓以其獨特的思考模式顛覆傳統的平庸故事時,他卻反其道而行地用平庸的故事顛覆了一個特立獨行的文本。這步數妙雖妙矣,不過若要用來挑逗觀眾的樂趣,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了。